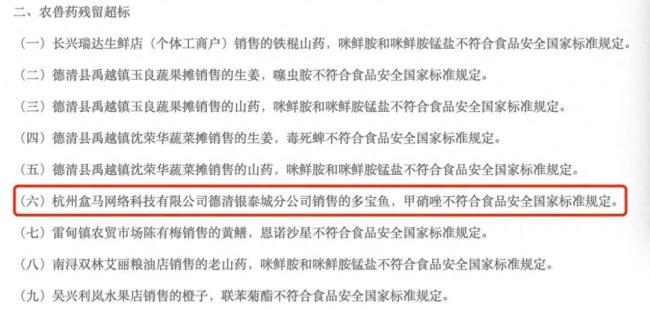机场回应摆渡车不通风有乘客晕倒
2025年7月11日晚,西宁曹家堡机场一架摆渡车内因高温导致乘客晕倒、车窗被砸的极端事件,将机场服务安全与乘客权益保障的矛盾推至舆论风口。机场以“航空器滑行安全”为由拒绝开门,乘客以“生命健康权”为诉求砸窗自救,这场看似对立的冲突背后,暴露出机场服务流程设计、应急管理机制与乘客基本需求保障之间的系统性断裂。
分论点一:安全规范与人性关怀的失衡,暴露服务流程设计的制度性缺陷
机场声明称,摆渡车停靠时因“北侧有航班滑行”而暂未开门,这一操作符合《民用机场航空器活动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则》中“防止航空器与车辆冲突”的要求。但问题在于,当乘客已出现缺氧晕倒的紧急状况时,机场仍机械执行“安全优先”原则,未启动任何应急预案。对比长春机场在严寒天气中提前开启空调、加密检修频次的措施,西宁机场的“安全操作”更像是一种“程序性冷漠”——既未通过车载广播向乘客解释安全风险,也未安排地勤人员安抚情绪,更未启动备用车辆转移乘客。这种“重流程、轻体验”的服务模式,本质上是将乘客视为“流程节点”而非“服务对象”,导致制度刚性挤压了人性温度。
分论点二:应急设施形同虚设,折射机场安全管理的形式主义痼疾
根据《机场摆渡车安全设施规范》,每辆摆渡车应配备4个安全锤、2个应急顶窗和1个应急出口。然而,在此次事件中,乘客需自行砸窗才能通风,暴露出两大问题:其一,应急设备维护缺位。有乘客反映“安全锤位置隐蔽”,而机场初步说明中未提及设备检查记录,暗示日常巡检可能流于形式;其二,应急培训流于表面。天津航空曾因摆渡车闷热被投诉,回应称“天气闷热导致体感温度高”,却未反思是否通过增加班次、优化调度等方式降低载客密度。当应急设施成为“摆设”、应急预案成为“纸面文章”,乘客的安全感便沦为制度空转的牺牲品。
分论点三:乘客自救权与机场管理权的边界模糊,亟待法律明确
乘客砸窗行为引发法律争议:支持者认为这是《民法典》第182条“紧急避险”的合法行使;反对者则援引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49条,质疑其是否构成“故意损毁财物”。类似争议在2021年天津航空摆渡车闷热事件中已现端倪,当时乘客投诉后,航空公司仅以“天气原因”搪塞,未触及管理权与自救权的法律边界。事实上,国际航空运输协会(IATA)在《机场服务标准》中明确:当乘客生命健康受到威胁时,可突破常规流程采取必要措施。我国《民用航空法》虽未直接规定,但可参照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11条“消费者享有安全保障权”,通过司法解释明确乘客在极端情况下的自救权边界,避免“合法维权”与“违法破坏”的模糊地带。
反论点驳斥:将责任归咎于“乘客过度维权”是转移矛盾的懒政思维
有观点认为,乘客应通过投诉、索赔等正规渠道解决问题,而非“暴力砸窗”。但数据显示,2024年全国机场服务投诉中,涉及摆渡车问题的占比达17%,而处理周期平均长达23天。当正规渠道效率低下、乘客在高温密闭空间中面临缺氧风险时,要求其保持“理性克制”无异于强人所难。更关键的是,此次事件中乘客并非主动破坏设施,而是在机场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后的被迫自救——若机场提前开启空调、及时沟通风险、启动备用车辆,冲突本可避免。
前瞻性建议:构建“技术预警+流程再造+法律兜底”的三维防控体系
破解这一困局需多管齐下:技术层面,推广“智能温控系统”,当车内温度超过28℃时自动开启通风,并通过车载屏幕实时显示温度、湿度数据,消除信息不对称;流程层面,修订《机场摆渡车服务规范》,明确“当乘客出现身体不适时,无论航空器状态如何,必须立即开门并启动应急预案”,同时将“乘客满意度”纳入机场考核指标;法律层面,由民航局联合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,明确“紧急避险”在航空场景中的适用标准,为乘客自救权划定法律红线。2024年上海浦东机场试点“摆渡车服务质量评价体系”后,乘客投诉率下降61%,证明制度改进的有效性。
从一瓶砸碎的车窗玻璃中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高温下的物理裂痕,更是服务理念与乘客需求之间的深层断裂。当机场以“安全”之名将乘客置于风险之中时,所谓的“规范”便沦为推卸责任的挡箭牌。唯有将“人”而非“流程”置于服务设计的核心,才能让摆渡车真正成为连接航站楼与飞机的“温暖通道”,而非暴露管理漏洞的“矛盾现场”。